2017年精选美文(2017年最佳小小说精选)
这条街把我迷倒了。
一个一个的小店,里头全部是花边。世界上,什么东西用得到花边呢?小女孩的蓬蓬裙,老婆婆的裤脚,轻女郎贴身的蕾丝胸罩,新娘的面纱,晚餐的桌巾,精致的手绢,让窗子变得美丽的窗帘,做梦的枕头套和床罩,教堂里烛台下的绣垫,演出结束时徐徐降下的舞台的幕,掌声响起前垂在鲜花下的流苏……各种大小剪裁,各种花式颜色的花边,挂满整个小店。店主正忙着剪一块布,头也不抬。他的店,好像在出售梦,美得惊心动魄。
然后是纽扣店。一个一个小店,里头全部是纽扣。从绿豆一样小的,到婴儿手掌一样大的;包了布的,那布的质地和花色千姿百态,不包布的,或凹凸有致,或形色多变。几百个、几千个、几万个、几十万个大大小小、花花绿绿的纽扣在小店里展出,每一个纽扣都在隐约暗示某一种意义的大开大合,一种迎接和排拒,仿佛一个策展人在做一个极大胆的、极挑衅的宣言。
然后是腰带店。一个一个小店,里头全部是腰带,皮的,布的,塑料的,金属的,长的,短的,宽的,窄的,柔软的,坚硬的,镂空的,适合埃及艳后的,适合小流氓的,像蟒蛇的身躯,像豹的背脊……
花边店、纽扣店、腰带店、毛线店、领店、袖店,到最后汇集到十三行路,变成一整条街的成衣店。在这里,领、袖、毛线、花边、腰带,像变魔术一样全部组合到位,纽扣扣上,一件一件衣服亮出来。零售商人来这里买衣服,一袋一袋塞得鼓胀的衣服装上车子,无数个轮子摩擦街面,发出轰轰的巨响,混着人声鼎沸,脚步杂沓。广州,老城虽然沧桑,仍有那万商云集的生动。
就在巷子里,我看见他。
一圈一圈的人,坐在凳子上,围着一张一张桌子,低头工作。一条巷子,变成工厂的手工区。他把一条手镯放在桌上,那种镀银的尼泊尔风格的手镯,雕着花,花瓣镂空。桌子中心有一堆金光闪闪的假钻,一粒大概只有一颗米粒的一半大。他左手按着手镯,右手拿着一支笔,笔尖是粘胶。他用笔尖吸起一粒假钻,将它填进手镯镂空的洞里。手镯的每一朵雕花有五个花瓣,他就填进五粒假钻。洞很小,假钻也很小,眼睛得看得仔细。凳子没有靠背,他的看起来很瘦弱的背,就一直向前驼着。
男孩今16岁,头发卷卷的,眼睛大大的。问他从哪里来,他羞涩地微笑,“自贡”。和父母来广州3个月了。
“他们都以为来广州赚钱容易,”坐在男孩隔壁的女人边工作边说,“其实很难啊。才16岁,应该继续读书啊。”
女人责备的语音里,带着怜惜。
“做这个,工钱怎么算?”
两个人都半晌不说话。过了一会儿,男孩说:“五粒一分钱。”他的头一直低着,眼睛盯着活儿,手不停。
“那你一天能挣多少?”
“二三十块,如果我连续做十几个小时。”
五粒一分钱,五十粒一毛钱,五百粒一块钱,五千粒十块钱,一万粒二十块。一万五千粒三十块。
那手镯,在香港庙街和台北士林夜市的地摊,甚至在法兰克福的跳蚤市场,都买得到。我从来没想过,手镯,是从这样的巷子里出来的。
很想摸摸孩子的头发,很想。但是我只说了句“谢谢”,就走了。
巷子很深,转角处,一个老人坐在矮凳上,戴着老花眼镜,低头修一只断了跟的高跟鞋;地上一个收音机,正放着缠绵的粤曲,一只猫,卧着听。

一条长江,分开了南北,从此,江北就有了豪爽,江南便添了含蓄,江北遍野是健壮着的江北,江南处处有柔媚了的江南,就是这样刚柔着的了啊,江南江北就这样刚柔成了古中国既对峙又融洽的同母姊妹。姐姐在江之北的渺袤平原,妹妹在江之南的烟淼水乡。平原厚实,那是江北世世代代淳朴的厚实,黄土很黄,黄黄地迷茫又迷人;水乡淡雅,自是江南祖祖辈辈悠然的淡雅,涟涟地漾着千年的风物与风华。江北是秦腔的江北,京腔是江北着的京腔,江南自是苏小小的江南,是唐伯虎绣口点秋香姑娘的江南了。唯在中秋,江南江北,同一轮明月,共听长江长了还长,齐吟黄河奔腾腾地金黄。或在元宵,将一锅汤圆,煮成五千年不变的团团圆圆与沸沸扬扬。这便是我的同时抚摩着江南与江北的万里长江了,在那年,被李白的轻舟飞过的那些激流与波澜。
想起江南,总是在黄昏,那烟那雾那雨那水,那永不凋谢的彩虹下面,明明朗朗地走着红红绿绿天下最美的江南女子,在歌,歌在花丛,歌在水边,歌在烟雨的江南,渺雾的江南,琴棋书画之后悄悄绣着鸳鸯蝴蝶的江南。那当然是祖母的功劳,纺车的吱呀,童谣的喃喃,水波粼粼,肥鱼鳞鳞,歌儿铃铃,纤纤的手儿也灵灵的江南女子噢,多想娶回家的娇柔得像莲花般的妹妹,采桑,养蚕,织布,浣衣,蓝花花的头巾,竹丝丝的斗笠,红蝴蝶又绿蝴蝶的发结,还有那羞红那笑魇那情魅,总是在我的梦中羞答答地开放,缓缓而悠悠地飘着奇香。江南女子,江南宝贝,妹妹又魅魅,媚媚还湄湄,雨一样的轻轻,雾一样地盈盈,从此不会再愤愤沉掉那只装了百宝的箱子,不再变作白蛇,不再流着血泪哀哀化蝶。
江南女子,单是汉字,就已构成视觉上的美丽了;单是音节,就已充满听觉上的温柔了,两千多年依然无可代替,浓艳着春秋五霸、战国七雄、秦王汉武、唐宗宋祖、燕赵豪杰、齐鲁英雄乃至一代代江南才子不眠的夜晚。两千多年,日月轮回,桑海沧田,斗转星移,你居然让那么多皇帝老儿从此不早朝。不早朝,就暗怨着退朝而去,一次次升起来的,是边地的烽火与战火,是得得的马蹄,隆隆的战车,胡人之后又竖起了满人的大旗,飒飒猎猎飘过江南。你的家乡,米是康熙的米,鱼是乾隆的鱼,整整三百年的清朝,江南女子,勤劳的妹妹,那日日夜夜旋转的纺车在为谁而摇?一片厚土,慢慢地被梦的手儿撕了千年,终于撕成了一条运河,沟通了南北,扬起了如诗如云的船帆,也运瘦了江南,剩下些烟和雨,飘在扬州,袅袅地冷着江南大地。苏州城的霓虹,杭州城的绿水,扬州城的玲珑而繁华的码头,江南女子的女子,江南妹妹的妹妹,一曲江南丝竹,千声冷雨芭蕉,凄清、凄艳又凄绝地为骑鹤而来的哥哥彻夜把酒。把酒,可曾问过青天?可曾孤灯残烛对影成了三人?人呢?人在何处?可是板桥?可是伯虎?或者是张生?不,张生等候在杜十娘的雕花窗下,任夜雨洗去苦恋的泪痕。苏东坡当然也来过,还有风流乾隆和慕名而来的开封少年、江湖游侠、京都公子、纨绔子弟……江南妹妹的妹妹,在运河的那头,拉纤的汉子;在边关的那边,守疆的汉子;在花城那里,开店的汉子……到底有没有你久盼不归的人儿?若是真的久久没有归来,有谁陪你撑着伞温馨地走过漫长的雨季?又有谁能够理解“锦书难托”?繁华的江南,热闹的江南,孤独寸心知,寂寞谁能解?我的江南妹妹呵,寐寐是不是总是难以成寐?……
江南女子,生得美丽又生于美丽,心不想齐天,命不愿如纸,只想该耕的就耕,该织的就织,只愿在方方块块的江南,在水一方的江南,烟雨迷朦的江南,杨柳依依的江南,杏花梨花桃花樱花的江南和紫燕剪春雨丝竹弄管弦的江南,为人贤妻,做人良母。
走进了江南,这才发现江南的女子果然这么好命,果然这么福气。苏州的桥,扬州的河,还有水乡的款款清流,小小的船儿,全都载着江南的女子,歌谣着过来,又歌谣着过去,拖一路长长的波纹,弯弯地就到了自家的门前。浅浅的岸上,稚童的额顶留着的是一小片青瓦,胖如莲藕的小手,在帮助爹娘系缆。上得岸来,当然有鱼有虾有蟹,还有莲荷,还有红杏,最是少不了的就是绣花的绸缎剪花的粉纸。于是,稚童在前,爹娘在后,在回家的路上走成一幅天伦之乐的江南图画。
家,当然是江南水乡的那种建筑,瓦青青,一片一片,组接成了鳞片一样整齐的沟沟与槽槽,这样的青瓦,最美之时是雨点密密地敲打,那声音,疑是白居易在夜船上听的那曲琵琶还没有收场。墙很白,远远地望去,以为挂了许多银幕,以为今晚要放映千部万部电影,最是不要放的是《南京大屠杀》,血腥的场面,兽性的枪杀啊刀杀啊火杀啊,与这样的江南,与这样的水乡,太不协调太不和谐了,最好是放映《天鹅湖》,让成群的美女化作成群的天鹅,柔媚地舞从容地飞,或者,放一部《天仙配》,让天上的祥云,人间的紫烟,就这么云牵烟绕。家家的白墙,家家的银幕,家家的《天鹅湖》啊家家的《天仙配》。窗是雕花的窗,镶千年的传说,嵌梦想的故事,方方正正,永远三维的象形文字,牵帘,看疏雨梧桐,嗅金兰幽香,听黄鹂与喜鹊报春和报喜的歌声,或者推开窗儿,唤狗,唤鸡,唤儿,唤邻居的闺女绣的牡丹该怎么配色,或者虚掩花窗,静静地等梦中人儿熟悉的脚步声声响起。
江南的赶集,最是一道风景,弯弯的拱桥上,江南女子,三五成群,花花绿绿,叽叽喳喳,人在桥上,影在水里,涟漪荡漾,江南的女子就全都在水面舞蹈。来到集市,蜜桃也好密桔也好枇杷也好,只叫名儿,不说价钱,还的多少就是多少,从不开价也从不讨价。卖完水果,她们就来到布店,扯一截花布,或绿或红,身上一披,就蓦然幻化成了一群仙国的孔雀。然后,一路有笑有歌,走过一块块菜花地,走过一座座石拱桥,走过一棵棵绿柳树,天女散花一样,朵朵又朵朵飘进了自家贴满了福禄寿禧的家门。
江南的女子,江南的妹妹,上像、入画、进歌,无论怎么着,都是最最中国的女子了,最最东方的女子了。刻在屏上,她能笑;绣入绢里,她能舞;玉雕成塑像,她就能立体成多情的江南,永美成妖娆的江南。而江南呢,因此不老,因此不衰,因此就在长江之南妩媚着、娇羞着、温柔着、不变地青春着了。江南的女子,女子的江南,美艳在长江南岸,那广袤,那肥沃,那富饶,一朵朵,一簇簇,锦绣了大中国迷人诱人醉人的江南。
秦文君:我们是一家人 阅读行动 2018.8.22我进中学时就开始盼望独立,甚至跟母亲提出要在大房间中隔出一方天地,安个门,并在门上贴一张“闲人免进”的纸条。不用说,母亲坚决不同意,她最有力的话就是:“我们是一家人。”
当时,学校里有位姓毛的女生,借居在婶婶家,但不在那儿搭伙,我看她的那种单身生活很洒脱,常在小吃店买吃的,最主要的是有一种自己做主的豪气,这正是我最向往的。也许我叙说这一切时的表情刺痛了母亲的心,她怪我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我说:“为何不让我试试呢?”见母亲摇头,我很伤心,干脆饿了一顿以示抗议。母亲那时对我怀了一种复杂的情感,她认为我有叛逆倾向,所以也硬下心肠,准备让我碰壁,然后回心转意当个好女儿。于是,母亲改变初衷,答应让我分伙一个月。我把母亲给我的钱分成30份,我想就不会挨饿了。
刚开始那几天,我感觉好极了,买些面包、红肠独自吃着,进餐时还铺上餐巾,捧一本书,就像一个独立的女孩,心里充满那种自由的快乐。家人在饭桌上吃饭,不时地看我。而且有了好菜,母亲也邀我去尝尝,但我一概婉拒。倒不是不领情,而是怕退一步,就会前功尽弃。
这样自由自在地过了半个来月,我忽然发现自己与家人没什么关系了。过去大家总在饭桌上说说笑笑;现在,这些欢乐消失了。
天气忽然冷下来,我感冒了,头昏脑胀,牙还疼个没完,出了校门就奔回家。家人正在灯下聚首,饭桌上是热气腾腾的排骨汤。母亲并不知道我还饿着,只顾忙碌着。这时候,我的泪水掉了下来。我翻着书,把书竖起来挡住家人的视线,咬着牙,悄悄地吞食书包里那块隔夜的硬面包,心想:“无论如何得挨过这一个月。”
到这个月的最后一天,早晨我就断了炊,喝了点开水,一个上午饥肠辘辘。放学回家,推开房门,不由大吃一惊,母亲没去上班,正一碗一碗地往桌上端菜,家里香气四溢,仿佛要宴请什么贵宾。母亲在我以往坐的位置上放了一副筷子,示意我可以坐到桌边吃饭。我犹豫着,感觉到这样一来就成了可笑的话柄。母亲没有强拉,悄悄递给我一个面包,说:“你不愿意破例,就吃面包吧,只是别饿坏了。”
我接过面包,手无力地颤抖着,心里涌动着一种酸楚的感觉,不由想起母亲说的话——我们是一家人。那句话刻骨铭心,永世难忘。
事后我才知道,母亲那天没心思上班,请假在家,要帮助她的孩子走出困境。当晚,一家人又在灯下共进晚餐。与亲人同心同德,就如沐浴在阳光下,松弛而又温暖。
如今,我早已真正另立门户,可时常会走很远的路回到母亲身边,一家人围坐在灯下吃一顿饭。饭菜虽朴素但心中充满温情,就因为我们是一家人,是一家人!
人长大后都是要独立的,可家和家人却是永远的大后方,永远的爱和永远的归宿。
李汉荣:伞铺街 阅读行动 2018.8.23人在天日晴爽的时候,常常是记不起伞的。所以先人才留下了叮咛:饱带干粮晴带雨伞。这句朴素的老话,被一辈辈人们重复着。
“闺女,出门别忘带把伞。”
“娘,我记住了。”
“我儿,伞在门后挂着,记住走时带上。”
“爹,我会带上的。”
就这样,叮嘱带伞的爹娘走远了,记着带伞的儿女也走远了,一代代的人都打着伞走远了。
只有上苍把下不完的雨,藏在江里海里,存在云里雾里,准备在每一个人的路上,随时泼下来。
所以,当我每一次走过伞铺街,我的眼睛似乎突然有了重瞳,有了多重视力,我从临街的门里看到了更多的门,从院子里看到了更深的院子,从人群里看见了更多的人群,从已没有伞的门面上看见了很多的伞,很多年代的伞,很多样式的伞。我看见木伞、荷叶伞、棕皮伞、布伞、油布伞、尼龙伞;我看见了唐朝制伞的人,宋朝卖伞的人,清朝修伞的人,民国打伞的人,我还看见不知哪个朝代的粗心后生,可能是唐朝吧,那是个气魄宏大、情思奔放的年代,这后生有点大大咧咧,出门忘了带伞,走到半路下雨了,他衣衫都湿了,路途遥远,雨还在下,没有停下来的意思,于是,他在雨地里跑着,差点撞着了一个挑着一筐韭菜叫卖的老汉,他慌忙道歉,他终于找到了伞铺街,他走进了卖伞的铺子,当他谢过店家,打着伞上路,那雨点儿打在伞上,就有点平平仄仄的韵味了,一首唐诗,而且是一首意境温润、对仗工稳的律诗,就在伞下问世了。我还看见,那是民国,新式的“洋伞”刚刚流行,伞铺街也突然洋气起来了,那一对年轻人紧挨着走在一个伞下,男的举着伞,女的手里还拿着一本书,在雨点儿的掩护下,他们说着生活的烦恼和打算,倾诉着细微的情感,时大时小的雨落在伞上,时而砰砰飒飒,时而滴滴答答,有时,哗啦啦,一下子就把伞上的积雨洒下来,好像把青春的苦闷都洒下来了——这变化着的雨声,恰到好处地掩护了他们一路的交谈和小小的秘密,他们就在那雨声里渐渐走远,走远。
就这样,走在伞铺街上,我总是遇见世世代代在雨里打着伞走过去的人,我总是听见伞下的低语、细碎的脚步和小小的秘密,那遥远的过去年代的雨,斜斜地飘过来,一次次把我的心悄悄打湿。而更多的伞刚刚举过来,又匆匆走过去,就随着一个朝代走进了历史的深夜。
我真想,让时光回流一小会儿,我要走进那个穿着一袭青衫的古代书生的伞下,与他交流对雨的看法和对时间的理解,然后,一起去赶考,去漫游,去登高望远,在高高的山顶,在雨后的白云上,写一卷新诗。
可是,当我把心里的羽毛收拢,安静地站在如今已没有伞铺的伞铺街上,安静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,安静地听着起起伏伏的市声,我听见的却不是高亢的浩歌,也不是豪华的话题,我听见的却是世世代代说了千百年的那些朴素的老话,从时光的门后,从历史的院落,从深深的天井,清晰地、恳切地、潮润地传过来:
“闺女,出门别忘带把伞。”
“娘,我记住了。”
“我儿,伞在门后挂着,记住走时带上。”
“爹,我会带上的……”
蒋方舟:莫高窟的挣扎 阅读行动 2018.8.24人生从未如此文化苦旅过,前段时间,我重走了丝绸之路。真是苦旅,戈壁沙漠再辉煌壮丽,一成不变的景色看久了,即便是王维,也吟不出什么新的诗句。
西域的入口是敦煌,僧人求法之旅从这里开始。当我在大马路上饥寒交迫接近绝望的时候,看到无尽的青黑天下压着金边,有夕阳霞光的地平线处就是敦煌,当时的场景就像电视剧《西游记》中的一幕,我好激动,马上想说的是:“大师兄,你快看,那就是敦煌。”
进了城,《西游记》里面奇诡的神秘文明,变成了现代化的摩登小城,紧凑洁净,饭馆的霓虹灯闪烁。擦肩而过的很多都是外国人,场景让人有穿越之感,它仿佛又变成了丝绸之路上中西贯通的重镇,异国商贾云集,胡人遍布。到敦煌当然是为了看莫高窟。我去之前,就有很多人告诉我:“莫高窟一定会让你觉得失望的。”乍一看,确实是如此,这里和中国其他旅游景区没有区别,到处都是戴着墨镜遮阳帽,满脸不耐烦地排队的旅客。人群里最大声的永远是小朋友的哭叫,都吵着要回家。
但我并没有失望,因为原本也不是为了寻找民族自豪感而来的。
四百多个洞窟只开放了二十多个,看完感受最深的是:美的事物总逃不过种种磨难,以及它自身求生的挣扎。
第一重磨难来自于自然。这里的雨少风大,强风把沙子吹到崖面。天长地久,入口处设置的窟檐逐渐磨损,失去了遮蔽阳光的功能。莫高窟高大,俯仰天地,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副衣不蔽体的模样。
第二重磨难来自于宗教变迁。佛教传入中国之后,经历过四次灭佛的劫难。最早是北魏太武帝:“各地有造佛像者诛,有经书焚烧,有僧侣悉坑之。”敦煌由于偏远,不仅没有受到废佛令的破坏,反而成为中西僧侣和教徒的避难所。他们把信念附在一斧一凿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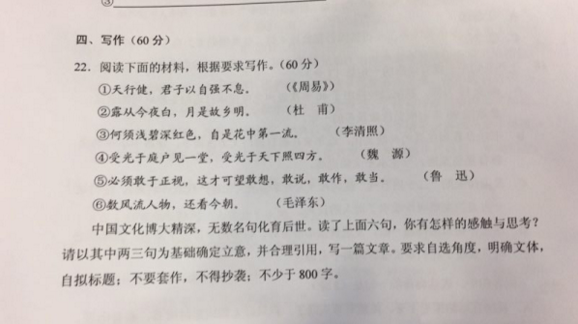
到了11世纪,新疆部分地区开始信奉伊斯兰教。佛教僧侣预感到劫难的可能性,就把数万件经书和藏画放在17窟中近千年。17窟就是著名的藏经洞,早就被洗劫,经书和佛像都已不在,只有当时藏经和尚洪辨的雕塑孤寂地守着空无一物的洞窟。
第三重磨难是“不懂”。大部分洞窟中的佛像都在清朝重新修过。绝美的壁画的围簇下,往往是呆滞死板的佛像,脸被涂得红红白白,一点表情都没有,眼珠是玻璃珠子,亮得又假又可疑,毫无动人之处。
开放参观的洞窟里,只有隋朝修的一窟佛像从未被重塑过,三座佛像,分别是“过去佛” “现在佛”“未来佛”。低眉的是弥勒,慈悲带笑,婉约悲悯至极。窟顶是直坠而下的飞天,飞天总是成双的,窟壁四周是撒满金粉的千佛像,现在金粉金箔脱落了大半。在这样的洞窟前,人一进去就有下跪的欲望——出于对美的诚惶诚恐。
第四重磨难是“不惜”。藏经洞被发现之后,当时看管莫高窟的王道士成了千古罪人。
历史上真实的王道士,虽然不懂,但是他爱惜。他先是看到官府在运输他至爱的经书时造成破损,看到送给当地官员的精品文物下落不明,然后他才变成了所谓的“卖国贼”。到了“文革”,当时莫高窟的48位工作人员分裂成大约12个革命派系,成天激烈内斗,所幸他们都同意一个原则:不能碰莫高窟。据说他们为了保护莫高窟,钉死了莫高窟所有的出入口。
我想起清洗竹简上泥土的场景:当把竹简放入清洁剂中,字开始浮现,有的字开始从竹简表面脱落,像是在逃生。天下没有永恒的事物,美的文明不被发现就没有意义,可它暴露的一瞬间就面临着巨大的风险,就像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”一样,它必然要经历更多的磨难,几番挣扎求生才能活下来。
获取更多美文,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阅读行动”。
踩一下[0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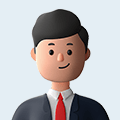 admin
admin
顶一下[0]